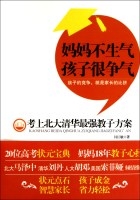我觉得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击,但也立即定了神,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
临末,我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风径奔通俗图书馆。
在那里看见《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这使我一惊,仿佛得了一点生气。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
我开始去访问久已不相闻问的熟人,但这也不过一两次;他们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却觉得寒冽。夜间,便蜷伏在比冰还冷的冷屋中。
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
然而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
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就在这样一个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没精打采地回来,一看见寓所的门,也照常更加丧气,使脚步放得更缓。但终于走进自己的屋子里了,没有灯火;摸火柴点起来时,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正在错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
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
“她去了么?”过了些时,我只问出这样一句话。
“她去了。”
“她,——她可说什么?”
“没说什么。单是托我见你回来时告诉你,说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清疏,在证明着它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
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
躺着,在合着的眼前经过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经现尽;暗中忽然仿佛看见一堆食物,这之后,便浮出一个子君的灰黄的脸来,睁了孩子气的眼睛,恳托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么也没有了。
但我的心却又觉得沉重。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
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终,还希望我维持较久的生活。
我要离开吉兆胡同,在这里是异样的空虚和寂寞。我想,只要离开这里,子君便如还在我的身边;至少,也如还在城中,有一天,将要出乎意表地访我,像住在会馆时候似的。
然而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我不得已,只好访问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经出名的拔贡,寓京很久,交游也广阔的。
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罢,一登门便很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我们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这里了,”他听了我托他在别处觅事之后,冷冷地说,“但那里去呢?很难。——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惊得没有话。
“真的?”我终于不自觉地问。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经忘却了怎样辞别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说谎话的;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像去年那样。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自然,我不能在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到来,无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
我比先前已经不大出门,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死的寂静有时也自己战栗,自己退藏,于是在这绝续之交,便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阴沉的上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耳中听到细碎的步声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睁开眼。大致一看,屋子里还是空虚;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
我一细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
那是阿随。它回来了。
我的离开吉兆胡同,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弟兄
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秦益堂捧着水烟筒咳得喘不过气来,大家也只得住口。久之,他抬起紫涨着的脸来了,还是气喘吁吁的,说:
“到昨天,他们又打起架来了,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他生着几根花白胡子的嘴唇还抖着。“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
“你看,还是为钱,”张沛君就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
“像你们的弟兄,那里有呢。”益堂说。
“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
“那里。”益堂摇头说。
“这大概也怕不成。”汪月生说,于是恭敬地看着沛君的眼,“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
“他们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益堂说。
“令弟仍然是忙?”月生问。
“还是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直忙不过来。这几天可是请假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
“我看这倒该小心些,”月生郑重地说。“今天的报上就说,现在时症流行。”
“什么时症呢?”沛君吃惊了,赶忙地问。
“那我可说不清了。记得是什么热罢。”
沛君迈开步就奔向阅报室去。
“真是少有的,”月生目送他飞奔出去之后,向着秦益堂赞叹着。“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
“说是折在公债票上的钱不能开公账。”益堂将纸煤子插在纸煤管子里,恨恨地说。
办公室中暂时的寂静,不久就被沛君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震破了。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说话有些口吃了,声音也发着抖。他叫听差打电话给普悌思普大夫,请他即刻到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
月生便知道他很着急,因为向来知道他虽然相信西医,而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于是迎了出去,只见他脸色青青的站在外面听听差打电话。
“怎么了?”
“报上说……说流行的是猩……猩红热。我我午后来局的时,靖甫就是满脸通红。已经出门了么?请……请他们打电话找,请他即刻来,同兴公寓,同兴公寓。”
他听听差打完电话,便奔进办公室,取了帽子。汪月生也代为着急,跟了进去。
“局长来时,请给我请假,说家里有病人,看医生。”他胡乱点着头,说。
“你去就是。局长也未必来。”月生说。
但是他似乎没有听到,已经奔出去了。
他到路上,已不再较量车价如平时一般,一看见一个稍微壮大,似乎能走的车夫,问过价钱,便一脚跨上车去,道,“好。只要给我快走!”
公寓却如平时一般,很平安,寂静;一个小伙计仍旧坐在门外拉胡琴。他走进他兄弟的卧室,觉得心跳得更利害,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而且发喘。他伸手去一摸他的头,又热得炙手。
“不知道是什么病?不要紧罢?”靖甫问,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不寻常了。
“不要紧的,伤风罢了。”他支梧着回答说。
他平时是专爱破除迷信的,但此时却觉得靖甫的样子和说话都有些不祥,仿佛病人自己就有了什么豫感。这思想更使他不安,立即走出,轻轻地叫了伙计,使他打电话去问医院:可曾找到了普大夫?
“就是啦,就是啦。还没有找到。”伙计在电话口边说。
沛君不但坐不稳,这时连立也不稳了;但他在焦急中,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
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白问山却毫不介意,立刻戴起玳瑁边墨晶眼镜,同到靖甫的房里来。他诊过脉,在脸上端详一回,又翻开衣服看了胸部,便从从容容地告辞。沛君跟在后面,一直到他的房里。
他请沛君坐下,却是不开口。
“问山兄,舍弟究竟是……?”他忍不住发问了。
“红斑痧。你看他已经‘见点’了。”
“那么,不是猩红热?”沛君有些高兴起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这立刻使他手脚觉得发冷。
“可以医么?”他愁苦地问。
“可以。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
他已经胡涂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竟请白问山开了药方,从他房里走出;但当经过电话机旁的时候,却又记起普大夫来了。他仍然去问医院,答说已经找到了,可是很忙,怕去得晚,须待明天早晨也说不定的。然而他还叮嘱他要今天一定到。
他走进房去点起灯来看,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他坐着,却似乎所坐的是针毡;在夜的渐就寂静中,在他的翘望中,每一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更使他听得分明,有时竟无端疑为普大夫的汽车,跳起来去迎接。但是他还未走到门口,那汽车却早经驶过去了;惘然地回身,经过院落时,见皓月已经西升,邻家的一株古槐,便投影地上,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
突然一声乌鸦叫。这是他平日常常听到的;那古槐上就有三四个乌鸦窠。但他现在却吓得几乎站住了,心惊肉跳地轻轻地走进靖甫的房里时,见他闭了眼躺着,满脸仿佛都见得浮肿;但没有睡,大概是听到脚步声了,忽然张开眼来,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地凄怆地发闪。
“信么?”靖甫问。
“不,不。是我。”他吃惊,有些失措,吃吃地说,“是我。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好得快一点。他还没有来。”
靖甫不答话,合了眼。他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一切都静寂,只听得病人的急促的呼吸声,和闹钟的札札地作响。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罢,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