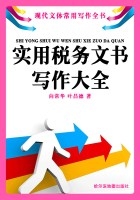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还在睡梦中的龚小诺被兜头一桶水浇醒。
“看你睡到不错。”纳兰浩然站在囚车边上,身边还跟着两手提着木桶绑架龚小诺的人。
看着她睡的安稳,他却一夜无眠,心里的无名火就直冲而上。
呛了两口水的龚小诺坐起身来,把湿漉漉的头发拨到身后,伸个懒腰,活动了下手脚,休息的确实不错,忽略伤口的话。
“是给我送药来了吗?”坐在满是水渍的囚车里,龚小诺懒的理会纳兰浩然的讥讽,男人,请不要那么幼稚。
“说你的条件。”她知道楼兰栈道的情况,也想到放火是种方法,但是这火怎么放,谁去放,出口怎么堵死,让他伤了一晚上的脑筋。
“我要他们俩死。”直视纳兰浩然阴翳的眼神,龚小诺扒在囚车的木栏边,笑着吐出让纳兰身边两人背脊发凉的话语。
“龚小诺,不要以为我杀不了你!”纳兰浩然伸手捏起龚小诺的下巴,他一只手就可以置她于死地。
“你输定了!”
龚小诺轻吐简短的一句话,却让纳兰浩然身边的人毛骨悚然。
她怎敢对纳兰将军说出这话,谁人都知,天朝的纳兰浩然将军从来没有战败过。
纳兰敛去笑容,手劲收紧,龚小诺吃疼的捏紧双拳,眼神未变笑容不改的盯着纳兰浩然。
“龚小诺,他们是我的人,谁都不要想动。”她可以提任何要求,除了这,猛和兽从小就跟在他身边,他纳兰不会拿自己兄弟的命做交易。
“那你就等着,你的部队为你陪葬吧。”她的心愿一向不大,以牙还牙而已。
“你……”
“将军,就让我们……”猛单膝跪地。
龚小诺好笑的斜睨着猛,这就是古人的愚忠。
她还以为是传说,若是把这人送给林纾,他该高枕无忧了吧!
“退下!这……有你们说话的份吗?”纳兰浩然打断并斥退猛。
他这生发过誓言,绝不让自己的兄弟窝囊送死,他们是军人,死也是要死在战场上的。
“将军,就让我们带上军将跟他们拼个死活,以我们的实力定是能胜。”兽不想看将军受制于人。
“敌伤一万,我亡八千,这叫险胜,也叫惨胜,和输有什么分别呢?纳兰浩然你的人,不是谁都不要想动吗?让他们送死你愿意?我的人也是一样,谁动了他就一定会付出代价,加倍。”
龚小诺话像千斤重的石块在每个人心里投下沉重的一击,击碎了所有人高傲的自信,如此的胜和败有什么区别?不禁自问,他们前赴后继的送死就能拿下苏呼尔敏吗?即使拿下,那又如何,不过是用尸骨堆集出来的胜利,得到也不过是一座鲜血染红的死城!这样有什么意义。
“龚小诺,你真是找死。”纳兰浩然见龚小诺的话祸了军心,心中狂怒,他明白她说的没错,都是实话,只是,说实话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纳兰浩然灌气于指,单手把龚小诺重重的甩了出去。
龚小诺犹如犹如脱线的风筝,身子飞出头重重的摔在木栏上,血顷刻间顺着脸颊和木栏间流了下来。
“你可真让我感动,我等着你们给我陪葬。”脸上的血触目惊心,流进了眼睛,染红了半边脸,龚小诺却任由血流着挑唇邪笑,笑的所有人都周身发怵,她就像扒开了地府之门,从里面跑出来的恶鬼,虽然受制于囚车,却让人惊悚,怕下一刻她就能破门而出要了人命。
他有碰不得的人,她也有。
“拿盐来。”纳兰浩然已被龚小诺的话激的失去理智,他一定会让她屈服的,如若不然乱了军心,士兵军心散涣,就是输了一半,仗也不用再打了。
“将军……”猛心有不忍,她还只是孩子。
“你想抗令?”猛跟了他如此多年,看来他也忘了事有轻重了。
“属下不敢。”猛抱拳请罪,他没有办法,如此不如要他的命,是他们先把她掳来的,其实一切都怪他和兽,她弄到如今这般田地根本是他们的错。
“无论胜负,仗完后,自己领五百军棍,来人,把盐抬过来。”吩咐了其他的人,纳兰浩然不再看跪在自己面前的,若猛般的妇人之仁,如何立军威。
“龚小诺,再问你一次,说还是不说。”
“将军长这么大没有求过人,也没有后悔过吧。”
“你想说什么?”
“将军今日一定要取了我的命,不然日后将军会后悔你今日求我的态度。”
“把……盐……给……我……化……开……了,泼!”他今天就要把这张刁嘴驯服顺了。
“得令。”
士兵手中的盐水没有半点犹豫,一桶桶的向囚车中的龚小诺泼去,血与浓稠的盐水渐渐的混合在了一起,湿透了龚小诺的全身,流出囚车滴在泥土里,囚车里龚小诺全身疼痛的不由的颤抖起来,伤口被盐水蜇的发红,身子像被一把把银针插她的筋,剜她的肉,刮她的骨,生疼猛烈的侵蚀了她所有的感官,龚小诺睁大的双眼也早就被蜇的全是血红。
她咬着牙,双手紧握囚车的木栏,不让自己叫出声音,不眨一眼的看着纳兰浩然,直到睁着眼疼晕过去。
“好了。”二十桶的盐水,泼的只剩两桶时,纳兰浩然终于悠然的叫了停。
囚车中龚小诺虽是睁着眼,可全身却已没了颤抖,看样子是昏了过去。“把她带到军医帐去,我要留活口。”
“是,将军。”得令的士兵打开了囚车,准备把龚小诺拖出来。
可谁也想不到的是,龚小诺的手紧紧的握着木栏,十指指甲都牢牢的陷进了木头,任凭士兵如何用力,那手都无法从木栏上掰下来。
迫的无法,最后只能叫了军医过来,在囚车里为龚小诺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