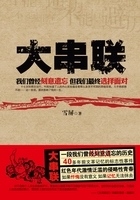那时他觉得自己像个父亲,每晚阿辽沙飞进他的帐篷时,他才感到这一天总算平安过去了——他真怕这孩子跟不上来。
而现在呢?现在他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他不知道,他自己也糊涂了。
刀尖陷进了皮肤,阿辽沙没有敢伸出手来阻挡,他紧闭的嘴唇哆嗦着,只是嗯了一声。一滴鲜红的血在刀尖头上冒了出来,在他娇嫩的乳头之间,顺着胸沟往下,流到他两侧带着沟窝的肚腹上。
巴烈亚柯夫男爵惊奇地发现自己开始喘不过气来,针刺一般的寒战从他全身的皮肤掠过,他的手指开始发麻。
噢——他狂吼一声,抽回匕首,狠命地往地上一掷。匕首插进地板里,噔的一声金属响,像手指碰着一根紧绷的弦,余音延续了很长。
七
到火车站接他的马车回到府邸,他老远就看见白大理石的门柱前,母亲站着等他。那是他从少年士官学校第一个暑假回来。
“母亲。”他从马车上跳下来,镇定地叫了一声,然后就身一侧想从母亲身边溜过。他知道母亲的拥抱亲吻会没完没了,挺窘的。但母亲只是用手里的扇子拍了一下他戴着军帽的头,说:“我的勇士,去吧。”
他冲进自己的房间,房间是熟悉的,但他觉得若有所失。坐了一会儿,他打开门偷偷往走廊里看,看见母亲站在走廊里,好像在等他出来。他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他们亲吻得直到泪流满面。
阿辽沙撑起手臂,俯在他耳朵上,对他说:“尼柯,尼柯。”
他从梦中醒过来,迷迷糊糊地说:“怎么?什么事?”
阿辽沙抱着他的头颈,抚弄他的胡须:“别把我留在后方。”
“唉,我的小勇士,你想干吗?”
“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他想了一下又说,“我要看打仗。”
他一下子醒过来了:“杀人有什么好看的?千万别去,你留在兵站。”
阿辽沙像只猫一样蜷缩进他的怀里,那一头火红的头发,柔软得像母亲金黄的长发。
阿辽沙说:“要是我跑了呢?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嗳,跑吧,兔崽子,跑吧。”
欧战即将开始时,士官团给了他三天假让他回家看母亲,母亲的脸容美丽而忧伤,但她很镇定,上战场本是俄罗斯贵族的特权:祖父在塞瓦斯托波尔负过重伤,失去一条手臂;父亲在对马海战中阵亡,让他很小就承袭了爵位。既被称作巴烈亚柯夫男爵,就是为了把血献给荣誉。
但是母亲说:“你得去看看柳芭。”
他在把自己七零八碎的东西收进抽屉里。好像打定主意不再回这间度过童年少年时期的房间了,他已经是军官了。
“柳芭,你得去看看她。”
他说:“我时间不够了,而且,为什么我要去看她?”
母亲说:“你们从小是朋友,我原以为她会成为你的未婚妻。”
不知为什么他听到这句话心里特别烦。他把抽屉砰的一声关上。母亲说:“你怎么啦?”
半晌,母亲坐到他身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已经十七岁了,你没有爱过什么姑娘吗?”
他摇摇头。
母亲又追问,好像有点着急似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
他吓了一跳,他抬起头,看见母亲满脸愁容。他说:“我就爱你一个女人。”
母亲转开脸:“快快打完仗,快快回来,我们再好好谈谈。”
可是母亲现在在哪里?他想,等这次战事结束,他得在伦敦和巴黎报纸上再登一轮寻人启事,他不能那么轻易地接受母亲已经消失这个事实。
但是,万一再次见到母亲,他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呢?她能接受面临的事实吗?
他睁开眼已是阳光满窗。这些士兵忘掉了晨操,他也忘掉了。母亲可能还担心爵位,这点暂可不必了。
八
四十七混成旅由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率领,很快进入蚌埠。
施从滨急于南进。桐城施家是安徽望族,他已经五十八岁,须眉皆白。袁世凯登基前封的陆军中将,却从来没有占住过地盘。壮士老去,机会方来。张作霖许他一个安徽善后督办的空衔,让他自己去从暴发户孙传芳手里抢安徽。他急于在孙军立足尚未稳时抢占津浦线,因此他狠命地催白俄团赶快跟上,渡过淮河占领门台、凤阳一线,掩护四十七旅东侧。
参谋处报告说白俄兵把基地设在符离集,从宿县往南,沿津浦线路东撒开一路,占着每个村镇榨钱,轮番递进一村一镇地榨,不交钱就杀人抢劫。白日抢钱财,夜里抢女人。因此前军至今还没到蚌埠北二十里的新马桥一线。
施从滨这才知道事情不太妙:张宗昌说把最精锐的白俄军队给他配合作战,说白俄军人高马大勇猛无敌,以前总是一露面就把对方吓唬住了。还说这个前锋团的团长是欧战和俄国内战中打出名的贵族军官,指挥有方,长于攻坚,保证能旗开得胜云云。
现在白俄军完全无意配合,他在蚌埠就孤军突出过前了。他的四十七旅残弱多欠饷久,无法独立支持。
施从滨非常恼火:这些俄国佬不知道打到南京苏州上海,抢钱抢女人才能抢出个名堂,在这个淮北穷乡乱抢个什么劲儿?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毛子。
当他知道孙传芳军的谢鸿勋师在西,卢香亭师在东,正形成三面包围蚌埠之势,便决定立即放弃蚌埠,全旅北退到固镇,而且不通知这些土匪毛子,让他们孤立在前与孙军作战,不管谁胜谁负对他都没坏处。
九
巴烈亚柯夫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就看见施从滨的联络参谋坐在他的指挥部里,死催活缠地要他早日进军。有时他不得不让巴沙把这个脸上表情过多的军官请出去。不过大部分时间不妨让他坐在那里:男爵和他的军官们俄语说得稍快一点,那人就一副懵懂。看来是北京速成俄专的什么学生。
可是,这天上午十时此人还没有出现。男爵突然想到可能情况有了变化。他立即叫巴沙和阿辽沙去找。他的侦察兵相貌太特别,言语不通,实际上摸不到任何情况。
阿辽沙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那该死的中国佬找不到,他和他的卫兵不知什么时候走掉了。那家房东几天前已被他们抓过来捆在后院牲口棚的柱子上,一直未能交出钱来赎回,家里只剩一个老仆人,说不清楚。
这时,向西搜索的骑兵也回来了,说津浦沿线已经空空荡荡,连驻守车站的四十七旅后卫部队也不见了。
男爵这才想到施从滨可能拿他做垫背的。现在敌情不清的情况下,只有从延伸到最南端的部队开始,稳步向北收缩。他立即命令团直属骑兵连与他一起赶到已经前行到磨盘庄一带的那半个营,组织后撤。
远远的,就听见南面响起密集的枪声。最坏的猜测被证实了,前出部队一旦被黏上,全团的后撤都成了困难的事。骑兵连用最快速度前进,快靠近村庄时,他看到左侧有一片略高一点的坡地,他命令骑兵连绕到坡地后隐蔽,自己带了警卫班冲上坡地观察战情。
从坡顶,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向村庄进攻的兵力不多,约两个连,数百人。孙军大部队没影子,或许在忙着占领蚌埠。
他定了定神。只要速战速决,脱离接触,就可备战迎敌。从1920年在乌拉尔与顿河一带恶战以来,还没有打过势均力敌的仗,尽被张作霖张宗昌用他们的大个头怪相貌来吓唬人,这次可能要动真刀真枪了。他立即命令传令兵告诉稍北驻新马桥的一营立即准备会合并后撤,骑兵连跟他从侧背袭击这股孙军。
他嗖地抽出马刀,全连都跟着他抽出马刀,噌噌地一片响。平原的劲风吹在钢刃上,擦出一种乐音。他脱下帽子,用袖口抹了下脸上的汗。不应该这么紧张,他对自己说。你是世袭俄罗斯军人,你跟号称世界最精良的德国陆军作过战,1914年在但能堡被围时,你曾带着小股部队冲了出来,尼古拉二世沙皇亲自签署给你的授勋令,把你从准尉见习军官立时提为上尉。
但他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紧张,阿辽沙在他身边,也抽出马刀在手。他从来没教过这孩子骑术和刀术,他完全没想让这孩子上战场。今天本应当先派他去执行较安全的任务,不知怎地,他与警卫班一起跟上来了。此刻阿辽沙正兴奋得满脸红光。
晚了,他想。他无法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好撒娇的孩子拉扯,全连都在看他的一举一动。
他侧过身望了一下,骑兵连正在他身后稍低处散开成一线,马喷响着鼻子,性急地刨着前蹄。他看到孙军的前沿已经向村庄发起冲锋,完全没有后续部队,留下几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开阔地。散散落落的村子里,不像有大部队跟上来的样子。
他咬了咬嘴唇,命令骑兵从坡地侧前直接冲入敌阵。
立时,一百多战马就在他眼前的田野上狂奔。秋种才不久的田野被踢起一面褐黄色的尘墙,等到一片震天的“乌拉”喊声响起时,他才带着警卫班冲入战场。他们顺坡而下,马跑得比骑兵连还快。他示意巴沙,让整个警卫班缓一步,除非万不得已,警卫班不应卷入战斗。只有阿辽沙不知是控制不住马还是什么原因,直冲在前头。
他非常恼火,他疾驰着,忙着观察战情,还得腾出眼睛余光看着阿辽沙。
孙军发现有骑兵突然从侧翼袭来,正在火力掩护下冲锋的部队立即停住,掉头往回跑,其余部队立即转向骑兵射击。他们还没布置好,骑兵已经赶到他们面前。田野里有些石块,马刀在石头上进出火星,吼喊和枪声把马刺激得分外疯狂,只倒下几匹马,骑兵已冲入对方散兵之中。孙军只能边打枪边往后撤,尽量向四面散开。
男爵看到阿辽沙的马正朝一个士兵冲过去。那个士兵开了一枪,没打中,一边拉枪栓一边往后跑。阿辽沙冲了上去,举起马刀迎头砍下,但马步与他的挥刀动作没有协调好。那个士兵听到马蹄声,回过头,及时用枪挡了一下马刀。当的一声,阿辽沙身子摇晃了一下,几乎被震下马来。此时马已经越过士兵往前跑去,阿辽沙赶快勒住马,转过马头。他的动作太慢,马不知所措地甩头晃脑。就在这时间,那士兵已举起枪对准阿辽沙的后背。
这个小子,男爵心里骂,还在玩耍呢!
他只稍稍夹了一下他的花斑马,马就很知意地从那个孙军士兵左侧作斜线奔过,男爵右手捏的马刀正好顺势轻轻地划了一道短弧线,切开了那个士兵的脖子。血呼啦一下喷了近半米远。他从正在与马较劲的阿辽沙身边跑过,愤怒地喊了一声:站着别再动!
阿辽沙满脸惊奇地看到临头的生命危险突然消失,那持枪者倒在地上,枪扔得好远,满地的血朝土里渗。他还没回过神来,不明白为什么男爵一脸凶狠。他的马不知应往哪个方向走,一蹶一蹶地挣扎,把阿辽沙颠得看不清任何东西。
骑兵连已经在包抄逃散的敌人,把他们驱向北,而北边庄里的部队已端了刺刀冲出来,与骑兵配合把敌军夹在中间。那些士兵似乎吓傻了,只听见零零星星的枪声,没有一个人在跑,的确已无处可跑,也没有继续抵抗的可能。
投降!男爵喊道:投降!他们都学过几个战场上最可能用到的中文词。但是没有一个人在缴敌人的械。在一片乱糟糟的叫嚷声中,只看见俄军骑兵和步兵从两个方向合拢,在全神贯注地杀人。巴沙挥舞着血淋淋的马刀,已经冲过战阵,又返回身来冲进敌人中间。有人举手投降。他从马上俯下身,把马刀狠狠地插进那个人的胸口,然后用力往下一按,那个人双手握住刀口,嘎声大叫,但他的内脏和手指一起落到地上。他向后翻倒,噗的一声,只剩一个腔壳,像空桶一般歪在地上。
我的上帝!他想,这是屠宰,这不是战斗。
他想叫停部队,赶快结束战斗准备后撤,可是看来也没有比杀光砍尽更快的结束战斗的办法。大部分敌人已被马队砍倒了,从庄里冲出的步兵正在宰杀最后的一批活人。
中国人打内战一向是尽可能多抓俘虏补充兵员,士兵总有投来降去的机会。他们没想到白俄部队不需要他们作兵员补充,没时间也没心思抓任何俘虏。不仅如此,俄国兵已经在搜杀伤员,用大刺刀朝喊叫的嘴一刀直插进去。抹血装死也没有用,俄兵正在把任何比较完整的尸体开膛破肚,骂骂咧咧地把嵌在骨缝里的刺刀往外拔,弄得满身血腥。
巴烈亚柯夫男爵看到过被炮弹炸碎炸烂的尸体,但没看到过这种结束战斗的办法。他知道他手下有不少人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些流氓,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狂醉地杀人。
他必须马上制止这种酷行:撤退已经不能再耽搁。
正在这时,他突然又想起阿辽沙。他转过头,看到阿辽沙的马孤零零地站在二百米远的地方。他心里突地紧揪了一下:怎么回事?他纵马跑过去,才看见阿辽沙站在马旁边,怔怔地看着地上躺着的那个士兵。那个人的头几乎完全被砍断,只是后颈还连着,血还在从头颈里伸出来的长短粗细不一的管子往外直冒。
忽然,阿辽沙提着刀蹲了下去。
别!别!男爵嚷了起来。在这一片喧闹之中,他的声音传不远。
当他勒住马,阿辽沙已经按住那个死掉的士兵的头,用刀子割,他的手被血染得通红。阿辽沙抬起头来,看见男爵在朝他走来,就咧嘴露齿几乎是白痴一样怪笑。
男爵觉得他的心在敲捶胸壁,几乎无法呼吸,他的脸色一定非常狰狞。他看见阿辽沙把那个头颅提起来。那士兵的头发太短,抓不住,只能抓住一只耳朵。血顺着阿辽沙的手臂流到肘上,他的军服上鲜血狼藉。他尖细的声音在狂喊:这个人差点打死我!这个人要杀我!这个人杀我!
他不知道阿辽沙脸上是汗还是眼泪,他只看见他的双眼充满恐怖,那两只曾让他看个不够的无邪的双眼,长着密密的女孩子一样的长睫毛,现在充满了恐怖:不是被杀的恐怖,而是杀人的恐怖。
他这才想起这个士兵本是他杀死的,赶快看自己的马刀,马刀尖上果然还有血。
一阵恶心带着酸水从胃里冲上来。你怎么啦?这又不是你第一次杀人。打了十多年仗你已经杀过不少人,再加一个又如何?战争不是杀人就是被杀。至于这个脏小孩阿辽沙,既然上了战场就得学会杀人。
这是你的错,他想。你根本就不应该优柔寡断,你早就应当赶他回后方。你白白糟蹋了一个孩子,他应当只是个孩子:天真,有一点儿坏心眼,有许许多多的缠绵。
十
他想起阿辽沙今天早晨与巴沙吵架来着,这才使他没有及早注意到施从滨联络参谋的失踪。
他记得阿辽沙正在卫兵室对着巴沙大叫大嚷,看见男爵走进指挥室,就迎着他跑了过来,嘴嘟得好高。
你怎么啦?他惊奇地问。巴沙是个嘴拙的人,不容易跟人吵架。尤其阿辽沙本是他的唯一好朋友。
“巴沙说我是赤党崽子!”
巴沙走上来,啪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团长,我只是说他父亲可能是赤党,流放到雅库茨克的大部分是政治犯。”
男爵说:“巴沙,我看你自己就是个赤党!”他走到摆好早餐的桌子边,“1917年你们顿河哥萨克部队最早响应布尔什维克,在前线罢战,杀了军官回乡。”
“我回了老家,但我没参加杀军官。”巴沙还是一板一眼,看来很老实地说着。
“那你瞎说阿辽沙又是为什么?”男爵问。
“我只是可怜这个孩子,”巴沙说,“政治犯流放苦役,说不定原来还是个好人家,念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