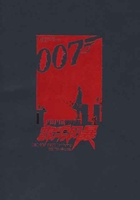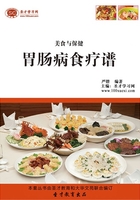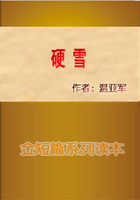性生于气,万物皆然。宋儒只为强成孟子性善之说,故离气而论性。使性之实不明于后世,而起诸儒之纷辩,是谁之过哉?明道先生曰:“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此三言者,于性极为明尽,而后之学者,梏于朱子本然、气质二性之说,而不致思,悲哉!(《王廷相集》第837页)
在宋儒中,王廷相服膺程颢性论,因为程颢性论以气为基础,反对气外别有性。宋儒皆尊崇孟子四端之说,以为人性本善,而以此善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故有“性即理”之说。王廷相多次指出,孟子性善论并不废性恶论。孟子说性善,是就人善的方面说,而人的不善的方面并非不存在。孟子说人皆有四端之心,就是从善的方面说,孟子说人之口要嗜美味,目要视美色,耳要听美声,四肢要安逸,此并非不是性。孟子以此种性为人与禽兽所共有,所以单指四端之心为性善的根据。这是为了给人指出一条“反身而诚”、“尽心知性知天”的便捷的修养途径。孟子并非以人出于形气的要求为非性。孟子说“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就是明证。所以王廷相指出:“是性之善与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论,而遗其所谓不正之说,岂非惑乎?意虽尊信孟子,不知反为孟子之累。”(《王廷相集》第850页)
王廷相认为,性中有善恶,性中善恶皆是气的作用,皆以气为基础。他说:
余以为人物之性无非气质所为者。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离性言气,则气非生动,与死同途。是性与气相资,而有不得相离者也。但主于气质,则性必有恶,而孟子性善之说不通矣。故又强出本然之性之论,趋于形气之外而不杂,以傅会于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论反为下乘,可乎哉?(《王廷相集》第518页)
王廷相将其气本论贯彻于一切处。既然性以气为基础,就不可能是仅有善而无恶的。程颐提出“性即理”之说,将人之善与宇宙根本法则会通,意在为性善论寻找天道上的根据。张载为了调和本然的人性和现实的人性的矛盾,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种性。天地之性出
于清通湛一的太虚,气质之性出于摩荡攻取的阴阳二气,“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朱熹继承了张载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之说,但以天地之性出于理,气质之性出于气,天地之性是宇宙伦理法则在人心里的表现,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受人的气禀的影响之后的表现。现实的人或
物,其天地之性为气质所遮蔽,须用存理去欲功夫,恢复天地之性。程颐、朱熹都承认有一个不基于气质的“天地之性”,虽说天地之性并不能离气质而存在,但天地之性却不来源于气。这与王廷相“性者,阳明之神理”的根本看法不同。王廷相公开表示自己在性论上与程颐、朱熹存在着矛盾:“程子以性为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王廷相集》第518页)他批评他的学生薛君采笃信程颐论性之说:
今君采之谈性也,一惟主于伊川,岂以先生之论苞罗造化,会通宇宙,凡见于言者尽合道妙,皆当守而信之,不须疑乎?(《王廷相集》第517页)
他也批评朱熹“性即理”之说: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由是言之,则性与气原是二物,气虽有存亡,而性之在气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气之聚散而为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王廷相集》第602页)
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即此数言,见先生论性劈头就差。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是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王廷相集》第851页)
在王廷相看来,人性以气为基础,故有善有恶。所不同者,圣人形气纯粹,所以圣人之性无不善,众人形气驳杂,所以其性多不善。但亦非全无善。人之善不是出于理,而是出于气。绝无在气外之性。
王廷相对性之动静中和亦有辩论。他反对《中庸》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更反对朱熹对于中和的解释。朱熹认为未发是性,是静;已发是情,是动。修养功夫在未发时涵养,已发时省察。动静皆主敬。王廷相认为,未发之中,只有少数圣人能达到,大多数人则难以企及,他说:
夫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惟圣人履道达顺,允执厥中,涵养精一。是以此心未发之时,一中自如,及其应事,无不中节矣。其余贤不肖、智愚,非太过则不及。虽积学累业,尚不能一有所得于中,安得先此未发而能中乎?(《王廷相集》第520页)
王廷相指出,《中庸》及朱熹性论之误,在于气质之上,另寻本然之性,作为未发之中的根据。应该在修养功夫之后求中。若不论修养功夫,不区别圣贤与庸众,以为皆有未发之中,则是不通之论。王廷相又批评了静善动恶之说:
问:“人心静未感物之时可以验性善,然乎?”曰:“否。大舜孔子吾能保其善矣,盗跖阳虎吾未敢以为然。何也?发于外者,皆氐乎中者也。此物何从而来哉?又假孰为之乎?谓跖也虎也心静而能善,则动而为恶,又何变之遽?夫静也,但恶之象未形尔,恶之根乎中者自若也。感即恶矣。诸儒以静而验性善者,类似圣贤成性体之也。以己而不以众,非通议矣。”(《王廷相集》第767页)
王廷相认为,动静不足以喻性情。静时未必皆性,静表心的状态和时序,性情则表善恶。庸众在未发时,恶已潜伏,只尚未形于外,不能谓之无,有感即恶形于外。这也就是王阳明所喻病虐之人,未发作时病已潜伏胸中,不可谓无病。以动静验善恶,是抹杀了圣贤和庸众的区别。王廷相反复申明,在人性论上他区别就性说性和并才气说性两种情况。前者他信从“十六字心传”,后者他信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单就性说,孟子所谓“良知”,舜之所谓“道心”,皆可征之于经验。如见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心中愧疚时额上出汗之类。但孟子所谓“天性之欲”,舜所谓“人心”,如“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四肢之于安逸”之类,亦可征之于经验。所以,性情二者,圣愚之所同赋。遵人心,庸众之最终归于恶;遵道心,圣贤最终归于善。道心人心皆有,可为“性相近”;差之毫厘而别以千里,可谓“习相远”。并且王廷相主要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反复说:“仲尼论性,固已备至而无遗矣。”(《王廷相集》第520页)
王廷相反对未发之中,反对静善动始有恶之说,有取于程颢。程颢曾说:“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论性,只是论‘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二程遗书》卷一)意为人只能据经验言性情。性属形而上,乃“人生而静以上”,在“言语道断,心行路绝”领域,不能言说。人所能言说的,只是形而下之气。形而上之性必于形而下之气上见,而形而下之气必对形而上之性有改变。“继之者”,是后天可经验之情。孟子正是从四端之情上论性善。王廷相有取于此,指出:“未形之前,不可得而言矣,谓之至善,何所据而论?既形之后,方有所谓性矣,谓恶非性具,何所以而来?程子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得之矣。”(《慎言·问成性篇》,《王廷相集》第765页)但王廷相对程颢说有极大改变。程颢“从情上见性”,王廷相则主“善恶皆性中本具”,完全出于其人生气禀论:“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所以王廷相对程颢之性论有取有舍,而对朱熹则几乎全屏矣。
王廷相也反对宋儒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他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对天命之谓性作了新的解释。他说:谓之天命者,本诸气所从出而言之也,非人能之也。故曰天也。性果出于气质,其得浊驳而生者,自禀夫为恶之具,非天与之而何哉?故曰“天命之谓性”。(《王廷相集》第519页)在他看来,天的本质是气,天以气赋予人,人禀天之气以为生命的基质。故说“天命之谓性”。性既为人、物禀受天之气而有,故气之性即人之性。气之性有纯驳,人之性有善恶。人之善恶皆由于气禀,非后天所致,后天只是改变或加强了先天为气所决定的善恶。所以,圣人之性纯善无恶,众人之性有善有恶,他说:
性之善恶,莫有过于圣人,而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禀清明纯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故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气之生理,一本之道也。(《王廷相集》第518页)
圣人之性纯善无恶,由于禀气皆清明纯粹;众人之性有善恶之杂,皆由其禀气之粹驳夹杂。
王廷相对人性的解释,由于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类文化长期发展塑造成的人的特质,完全以自然物质去解释人性,结果走入一偏之论,没有朱熹之性论从人之异于禽兽处着眼那样深刻、广大。朱熹在人性论上吸取了二程“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的原则,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人性学说。朱熹论性是从两个层次着眼的,即人作为一种高于任何生物族类的生命群体和作为物质构成的血肉之躯。朱熹所谓气质,非关善恶,主要是就强弱智愚等非伦理因素而言。朱熹的天命之性(或曰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继承了孟子和《中庸》。孟子不是简单地把动物性生理本能作为人的根本性质,而是把人看做高度发展了的特殊动物。人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发展出了维持族类生存所必需的伦理原则。这些伦理原则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纯粹化、神圣化,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它有足够的权威来管摄人心。宋明理学的性质之一,就是把伦理原则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并从人与宇宙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加以说明。所以张载、二程、朱熹这些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严格区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目的就在把作为人类伦理原则的那一部分和作为个体生命普遍具有的那一部分协调起来。人类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感到伦理原则的不可或缺、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把它定义为人的本质属性的。发现它,把它从人的生物性中提升出来、突出出来,这本身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既讲天命之性,又讲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在对人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比之把人性视为全部生物本能、感性活动的总和来,要深刻得多。突出天命之性,就是突出人的族类特征、社会特征。以这一特征为“天之所命”,并不是认为一个有人格的主宰者作出此安排,而是突出人的族类特征的不可抗拒并把用它来约束人的行为作为自律的活动。孟子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是把人本能的向善而不是现实的善作为人性善的根据。而这种“向善之本能”又是人在漫长的进化活动中对动物性中利于种群存在和延续的一点点好的东西突出、提纯、遗传、定性的结果。并把这种东西投射于宇宙万物之上,使之与人的期望相吻合并且反过来对培养人的善端起促进作用。这就是“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文化人类学含义。而所谓气质之性也不是像王廷相那样,指人得于气的全部属性,而只是指天命之性通过气质之性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的人性。所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分更能说明真实的人性,它比完全从气的方面去说明人性更有说服力。当然,对人的维持族类所必需的伦理原则强调过了头,就会扼杀人的个体性。对人的个体性、人的生物本能方面强调过了头,就会影响乃至破坏人作为群体的族类存在。人的全部生命智慧,就在既尊重和发扬人的族类伦理原则,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感性需求,做到二者的合理与调适。
三修养论
王廷相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在他的哲学著作《慎言》中有《作圣》、《潜心》、《君子》诸篇专论修养。他的修养论接触到许多方面。首先,他把人分为四种:圣人、亚圣、大贤和一般人。这四种人代表了道德修养的不同境界,不同层次。他说:
圣人,道德之宗正,仁义礼乐之宰摄,世固不获见之矣。其次莫如得亚圣者,契道之真,以命令于一世焉。其次莫如得大贤,严于守道,不惑以异端九流以乱道真焉。下此随波徇俗,私智害正者,纯疵交葛,吾不知其裨于道也。(《王廷相集》第762页)
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士人进德的标准,圣人是仁义礼乐的判定者和解释者。王廷相所称述的圣人,不过尧舜周公孔子数人。次一等的为亚圣。亚圣是契合圣人之道,以圣人之道教化斯人者。王廷相所称之亚圣,为颜渊与孟子二人。颜渊资质近圣人,孟子才能近圣人,而皆不为圣人者,由于二者不能兼而有之。圣贤之别,有许多方面,而最显著的,在圣人的道德修养与知识学养已达化境,与道为一而无迹可寻,故能无入而不自得。王廷相非常向往与赞美圣人之“化境”,他说:
从容纯熟,与道吻合,化也。学至于化,大之迹泯矣。而曰“化而后能有其大”,何也?大有迹也,犹有事于外也,在外犹有存亡也,安能保而有之?化则敛于精,贯于一矣。其出入由我也,故谓之有。(《王廷相集》第760页)
化是圣人最高境界,达此境界,修养已经纯熟,自然涌出,皆与道吻合,而又从容优游,无有穷探极取之象。《中庸》所谓“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正谓此种境界。此种境界,“大”不足以喻之,大犹有外在之迹,有迹犹滞于方所,无迹则与道婉转。达此境界就是主体精神最为昂扬之时,也就是赞天地之化育最为通达之时,王廷相形容这种境界:“惟圣人之道术不固挈于一,而参之,而衡之,而交午之,而翕张之,而迟速之,而括之,譬百川委委各至于海也。济务长功,安有穷已?”(《王廷相集》第762页)这是与道为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多有描画,王廷相的特殊之处在于把《中庸》、《易传》、《庄子》的圣人观结合起来:圣人不只是道德的极致,也是宇宙精神的象征。圣人既有大易的健动,又有《中庸》的中和,庄子的与道为一、与造化为功。王廷相的圣人观,是《论语》、《孟子》中的人文精神,《易传》、《中庸》中的宇宙精神和《庄子》中的自然精神的结合。
王廷相在圣人诸德性中特别看重与道为一,与时偕行,所以他强调“圣人因时”:
道无定在,故圣人因时。尧舜以禅受,汤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继序。道无穷尽,故圣人有不能。尧舜之事,有羲轩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尧舜未能行者。(《王廷相集》第7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