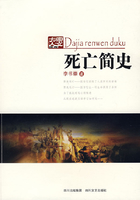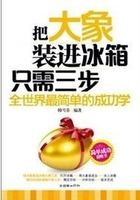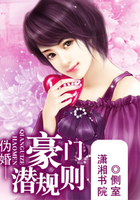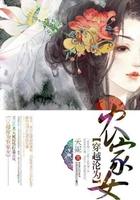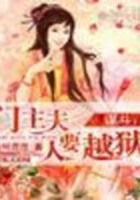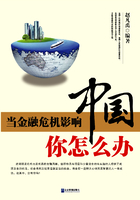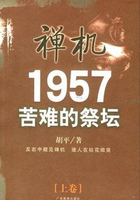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心本体论的又一层论证。“知行合一”是以“心即理”为基础而提出的,但与上一节的“心理合一”思想相比,它已不仅限于人性论、道德论的内容,而是着重于“心即理”在认识论方面的阐发,从而把“致良知”思想推进到认识论范围了。
“知行合一”的提出是在龙场悟道的次年(正德四年,1509年)。
当时王阳明应贵州提督学政席元山之聘主讲贵阳书院。此时,知行合一还没有成为王阳明论证的主题,只是在涉及朱陆异同之辨时提出的一种观点。三年以后,门人徐爱因不解“知行合一”之旨,与同门往复讨论不能解决,于是请问,王阳明才比较详尽地解释了“知行合一”的基本含义。他说: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传习录上》)
又说: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同上)晚年,在《答顾东桥书》中论及《大学》格物说的主旨时,王阳明又从“心”与“理”合一不二的关系上进一步阐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
又说: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同上)
他在这里指出,物理本来不外于吾心,这是“知行合一”说的根据;外心以求理,则是在实行道德时把知行分离的原因。而朱熹“即物穷理”说将心理分离,是导致“外心以求理”之风的病源。他又进而说明“学问思辨”之作为一种为学的程序,其每一步都贯穿着对“心之理”的实行,因而所谓“穷理”决不能脱离“行”,“穷理”就是“反求诸心”,即实行“良知”的功夫。他说: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
如方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者乎?学射则必张弓挟失,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
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提出亦是直接针对朱熹的。
朱熹用“即物穷理”解释大学的“格物”,将心与理对立,遂产生了在道德修养上只注重口耳讲说而不讲究身体力行的流弊。就此,王阳明把“知行合一”当作“对病的药”、“补偏救弊之言”。但他又指出,“知行合一”并不是其“凿空杜撰”,而是“知行本体”本来如此,“知行合一”决不仅只具有方法上的含义,而是对本体的论证,是对“心即理”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从这点上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又是直承陆九渊的。
陆九渊的“心即理”命题虽然将“理”主观化,使之接近于主观之“知”,但“理”并非即“知”,“心”与“理”也未达到完全的吻合。
陆九渊所谓“心”,在本体论上指“圣人之心”,“圣人之心”接近于“理”,其实也只是一种带有伦理实体性的道德意识。“心即理”将心、理等同,只是标出了一种心理境界,这种境界无疑是主客观合一的,但它只是人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在一瞬间的吻合。陆九渊要把这种境界贯彻到日常的道德践履之中,因此他主张为学修养除了“明心”的直觉体验外,还要补上“致知”的功夫,而这种“致知”又与朱熹的“穷理”致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陆九渊在认识论上沿袭了朱熹“知先行后”、“为学次第”等说法,表现了他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论上的不彻底性。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是为了弥补陆九渊“心即理”的这一缺陷。他在《答顾东桥书》中,除了批评朱熹“即物穷理”说“外心以求理”的路线,还特举《中庸》的“学问思辨行”来说明所谓“为学次第”,应该是“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
他指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所以凡“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都是与“心即理”的思想相悖的。这些思想虽是直接针对朱熹“格物”方法而提出,却也不能不说是有感于陆九渊“心即理”命题之不足而发。即是说,“知行合一”在理论上是面对着双重课题而提出:一是解决朱熹的“格物”说在修养方法上所产生的“心理为二”之弊;一是彻底铲除“外心以求理”的理论根源。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以上两点为依据,故他强调:其一,“知行本体合一”,指出“心”作为道德行为根源与认识根源的一致性、统一性;其二,知行“功夫”合一,从主体的心身关系上说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因而“格物”就要从主体的“身心”上用功,格物即是“诚意”,即在人的意念发动处做“为善去恶”的功夫。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二、知行本体合一
所谓“知行本体”主要指心、性、理与“知”的关系。“心”指道德活动的主体;“性”指以道德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活动机能,包括认知机能;“理”指道德理性,即心在道德活动中的体认对象。
王阳明把这三者合一为“知”,认为它是道德活动中即知即行的主体,又是认识和道德行为的最终根源。他提倡“心即理”,主张“至善”的“本体”只能到人心中去求,“心理是一个”,“此心在物则为理”(《传习录下》),其目的就是把朱熹哲学本体论中能够生成万物的“理”本体,换成与人的感官及认识直接联系的心本体和“知”本体,从而把道德修养与道德认识统一到一个根源上。他把“心即理”的思想衍作“知行本体”,这样就避免了陆九渊哲学中“心”与“理”之间所发生的歧义,进一步摆脱了朱熹之“理”的纠缠。
王阳明“知行本体”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知觉”之心与“主宰”之心
他把“知”作为“心之本体”,认为“心”的本质是知觉,而这种知觉的灵明性也就是对全身动静的主宰作用。他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同上)“心”没有形体,不是感官,只是一种能知的灵明性质,这种灵明性表现在对全身动静的主宰作用上:“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同上)
在认识主体方面,以心的能知作用和心对身的主宰关系来解释“心”,这是王阳明心学之“心”与朱熹理学之“心”基本相同的方面。但是,王阳明强调心的能知与主宰作用的统一,进而为心性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性即能知之性
与朱熹不同,王阳明把性也看作能知之性,从这点上,便把心性的意义统一起来了。他说:“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心性合一,人的生理与心理融为一体,他进而把生理当作心理的派生物,说:“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传习录上》)
“性之生理”是就心性合一而言的,“性”之所以叫作“心”,是因为它有“主宰一身”的作用,这就是“天理发生”。所谓“天理发生”,是说心的思维活动性能与这种性能产生的根源是统一的。王阳明认为,“心”与其所产生的意识活动不能分割,因此心性是一回事。但是他讲“天理发生”,还是就道德性讲的。“性”除了与“生”字相联系,在宋明理学中更重要的含义是指先验道德性。程朱“性即是理”的命题把封建道德性当作普遍的道德准则,并夸大为宇宙本体。程颢虽然特别重视这种道德性与“生”的关系,提出“识仁”,把“仁”看作“万物之生意”(《遗书》卷十一),即万物以生命为基础的感通作用及人的知觉作用;但所谓“仁”,其核心还是道德性,是“仁、义、礼、智、信”的全体和源泉。王阳明沿袭了“性”作为伦理本体而与心相通的意义。就此,他认为“性”是“心之本体”,是“知”的真正源泉。他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动,理原不动。”(《传习录上》)“知”是心之本体,“性”亦是心之本体,可见“心之本体”是“知”、“性”合一的产物。王阳明继承孟子的说法,把它叫作“良知”。他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他把心所固有的知觉当作一种道德灵觉,以此来说明人的认识来源,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上》)
(三)知是“理之灵处”
王阳明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即理”。他把心性合一于“知”,这样就改变了“理”的性质,使之由客观的理变为主观的理,即“心之理”。他把程子的“在物为理”头上添一“心”字,成为“此心在物则为理”(《传习录下》),表现了对“理”的性质的改变。
王阳明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传习录上》)
“知”是理的灵明处,主宰处为“心”,禀赋处叫作“性”,其实都只是一事。因此,心是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的,不必求之于外物。
他以为“天理”的“昭明灵觉”作用便是“良知”,良知包含了“心之本体”(认识主体)与“心之理”(体认对象)的双重含义,是一种圆满自足的认识本原,无所不该的宇宙本体。他说:“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传习录下》)他把“心、理合一之体”当作人的一切道德认识及道德行为的源泉,这也就是“知行合一”本体,而此“知行本体”是源于先验的道德性,即“不曾有私意隔断的”(《传习录上》)。
(四)“真己”为躯壳主宰
王阳明与弟子萧惠有一段对话,其中提出“真己”与“躯壳”
之己的关系问题,最能说明这个思想。今全文引录如下:
萧惠问:“己私难克,奈何?”
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又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萧惠曰:“惠亦颇有为己之心,不知缘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说汝有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谓颇有为己之心。今思之,看来亦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己,不曾为个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惠曰:“正是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声,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乐,所以不能克。”
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岂得是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时,便须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动;必须非礼勿视听言动,方成得个耳目口鼻四肢,这个才是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躯壳外面的物事。汝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礼勿视听耳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主体。”(《传习录上》)
王阳明所谓“真己”,即是具有先天道德本性之“己”,他与人体生命以及思维活动是共存的。人生,包括人的意识活动、认知机能是以人的生命为基础的,但它既已作为人的存在,便与其社会活动、道德伦理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便有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之存于人,自然能够支配人的视、听、言、动等感官活动。王阳明以此作为“知行合一”的根据,他所谓“知行本体”,无非是已经与人的心理活动融为一体的先验道德本性。这就是他所说的“真己”,他认为这个“真己”与“躯壳”的“己”并不矛盾,而是存在于其中。因此,所谓“知行本体合一”无非是把人的道德本性与其意识活动、认知机能融为一体,以作为实践道德的认识论根据。从这方面看,他的思想是不无合理之处的。问题是,他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伦理意识———封建道德当作先验的、不变的道德本性,这就不免误入歧途了。
三、知行功夫合一
知行功夫合一是王阳明从“心理合一”的观点出发对《大学》“格物”说的阐释,是把朱熹的“穷理”之学变成了落实于“身心”的实践功夫。他对于陆九渊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心即理”为原则,摒弃了其“知先行后”的说法,同时融进朱熹以日常生活中的事事物物为“格物”对象的实践道德方法,从而发展和完善了心学的道德修养论和认识论。王阳明说: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答友人问》,《全书》卷六)
他强调知行“原是一个头脑”,“知行合一”须是“头脑见得分明”,并承认这一点是自己与陆九渊的大同处。所谓“同”,其实即是同在“心即理”以“心”为本体,为“头脑”。在同一篇中,他亦不否认自己主张“知行合一”说是与朱陆之说各有异同的。兹录如下:
(问):“象山论学与晦庵大有同异,先生尝称象山‘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今观象山之论,却有谓学有讲明,有践履,及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乃与晦庵之说无异,而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答友人问》)
观此,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综合朱陆两家学说的结果,是以陆九渊的“心即理”为“头脑”,融入朱熹的“格物说”并对“格物穷理”之旨进行改造而成。在《答顾东桥书》中,他曾指出:“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传习录中》)这又表明他的“知行功夫合一”是针对朱熹“格物”说在后世所产生的弊病而对其进行改造的产物。
关于知行功夫之合一,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这是从知行存在于同一个认识主体及围绕着同一个目的、动机来讲的。他又说: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元来只是一个工夫。(《答友人问》)
这又是从知行贯穿着同一个意识活动及心理过程来讲的。王阳明把知、行合为一个主体——— “心”,他对知行合一过程的阐述也大多围绕着主体的意识活动进行。他对这些观点的阐发主要表现于对《大学》格物说的解释当中,述之如下:
(一)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
王阳明自称他的哲学为“身心”之学,其“知行合一”的奥秘也就在于把心学的心身关系论逐步扩大。他把个体意识的心身关系等同于认识与实践活动的知行关系,又由此扩大到心物关系,从而把客观存在的外物融合于主体道德践履的心身活动之中。
关于心与身的关系,王阳明认为,“心”处于支配地位,“身”只不过是“心”的充塞处、主宰对象无心则无身;反之,无身则无心。他说:
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答友人问》)
由此来看知与行,他以为所谓“知”、“行”,其实只是“心”对“身之灵明主宰”与“身”对“心之形体运用”的关系。在《大学问》中,他说:
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全书》卷二十六)
他把知行关系等同于心身关系,强调了主体意识活动在行为中的能动作用,但却排除了意识反映外界的客观内容。他又进而把这种心身———知行关系,扩大到心物关系方面,以为心身———知行———心物,没有什么不同,身、意、知、物都只是一件事。
他说:
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著处谓之物,只是一件。(《传习录下》)
用这种观点解释《大学》的“格物”与“修身”、“正心”、“诚意”诸功夫的关系,他以为“格物”和“修身”的根本在于“正心”、“诚意”;“诚意”和“正心”则要通过“修身”和“格物”的具体事物来体现。这样, “格、致、诚、正、修”诸功夫则是合一的,须同时进行。他说: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 《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当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
然……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故欲正其心在诚意。……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诚意功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传习录下》)
(二)“格物”即是“诚意”
“身、心、意、知、物”,其关键是个“意”字,“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王阳明在知行关系中突出“意”的范畴,用这种观点解释大学的“格物”说,他以为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意”,“诚意”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但他就知行关系上讲“意”、“知”、“物”的关系,其对“诚意”、“致知”、“格物”的解释却已经超出了《大学》的本意。
他举道德修养活动为例,说明“意”即“意欲”,指打算做某事的意念,“知”是做好事情的具体知识,“物”是所要做的事情。
“意”与“知”体现在“事”中,“诚意”、“致知”即在所要做的事中去实现符合“良知”的“意”,以达到知行的统一。他把这个过程叫作“格物”。他的“格物”说,把“意”与“知”这些属于意识活动的现象放到“事”的范围内来说明,而“事”不仅包含受主观意向支配的道德践履活动,也包含客观存在的事物。他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诚意”,也就是重视“意”对于知行以至心物的关系中所起的中间环节的作用。他把“诚意”之“意”进一步引申、发挥为知行关系中的意念之“意”,以此说明主观意念的能动作用。
意,即由“知”发“行”的主观意图。王阳明认为“知”与“行”合于“心之本体”的“良知”,而体现“知”的“意”也是由心产生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知”决定“行”,它对“行”的支配作用,主要体现在心对意念的发动过程中,意念发动之时,也就是行为的开始。他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也就是说,“心”对“物”的作用表现在知行关系中,一个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都首先决定于有没有此意念,一旦产生某种意念,就意味着即将开始某种行为,因此,“意”决定了事物的发生与进行的方向。心是发出意念的,而意念是决定行为方向的。因此意念便成了知行活动的主要对象。
(三)“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
王阳明把在意念发动处为善去恶作为知行合一的主要功夫,他曾说: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也是他把知行两种功夫合一的主要根据。这也正是他把主观活动之意念无限扩大,使之融合了“物”,吞并了认识和实践对象的结果。
这一过程是通过“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的命题来完成的。“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把作为客体存在的认识对象之“物”主观化,当成了主观意向的产物,心的派生物,从而对“物”的意义作了歪曲的理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混同了“物”与“事”的概念。我国古代,“物”除指“天地万物”外,也包含有“事”的含义。但严格地讲,“事”与“物”并不能等同。“事”包括了事行,即实践的内容,而事行、实践虽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却又不同于自然过程的客观之“物”,而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朱熹讲“格物致知”,即训“物”为“事”,他说:“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大学章句》经一章)“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朱子语类》卷十五)“衣食动作,只是物。”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王阳明继承了“物”的这种含义,他说: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这样,不仅混同了“物”与“事”的区别,而且进一步找出在“事”中与“物”即客观对象有密切联系的主观意识要素“意念”,以它来概括说明“物”,从而把“物”主观化,融合在主观意识之中。这是他把“物”的概念向主观方面发展的关键一步。
其次,他颠倒了“意”与“物”的关系。“意”与“物”,就认识的本来规律讲,无疑是“物”在先,“意”在后,“意”源于“物”。因为人们的主观意图、念虑作为主体的动机、目的,虽然代表了实践中的主观因素,但就其最终根源讲,还是源于对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是“物”的反映。王阳明却颠倒了这一关系。他以为意念是由有先验之知的“心”发出的,“意”来源于“心”的先验之知,而“物”是由“意”派生出来的,是“意之所用”。他说: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明白宣布主观意念所指就是物,若没有意念就无所谓物的存在了。由于对意、物概念的融合与对两者关系的颠倒,王阳明把知行功夫的重点进一步落实到意念上,把本来是注重“行”的知行合一方法变成只在主观意念上用功。他以为,只要从意念上彻底去掉恶的动机,就可以不用管实行的效果如何了。对于他这种极端的观点,以往的哲学家给予了诸多的批判,但他们往往抓住了这种思想在修养方法上与佛教禅宗“一念修行”、“念念若行”(《坛经·般若第二》)等说法的共同处,而忽略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本身的理论机制。其实,“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实践道德说的重要观点,是他从自己的生活实践及道德践履的切身体验中逐步形成,并从理论上滑向唯心主义的。他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只不过是在这个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某一点或某个环节,如果对此过分强调,便会忽视了“知行合一”说本身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