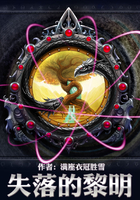他很快就把冰激凌吃完了,然后站起来买了一包烟,放在口袋里,在吃一碗方便面,走上楼去了——躲过楼门口的老太婆。
他迅速地被拉了进去。
接下来的时间他一直坐在桌子前面写作,飞快地写着,不时放下笔用毛巾揩手上的汗,六点过十五分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门铃,消失在窗口,几秒钟以后他出现了,半分钟以后他湿着头发站在窗户旁边,从抽屉里拿出钱包,仔细数出一百一十五块,然后再次消失了。
几分钟以后那个在永定街一带家喻户晓的收水电气费的女人穿着睡衣出现在楼门口,肩膀上露出发黄的内衣带子,她和旁边那个卖烟的寒暄了几句,走了——那个骂人的疯老太婆不知道去哪里了。
现在剧作家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了,睫毛意外长得很长——一张俊朗的脸,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平静而享受的神情,他小心翼翼地抽烟,每一口都吸得很深,每一根都抽到不能再抽然后熄灭,他很快把一包烟抽完了。
但他丝毫没有放松的样子,神色凝重,用手不停地往后梳着头发,但终于在边缘停住了。苍蝇们一拥而上。
四楼住的是三个附近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俊朗的脸上像是爬了一只毒蚊子那样透出隐隐恐惧,终于,他像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开始给什么人打电话,快速地说着一些话,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宠溺的神情,她左手抓着一个铲子,连连笑着,无疑在给某一个他所爱的姑娘说话,汗水湿透了他的背心,阳光并不大,但无处不在,大概五分钟以后他放下电话,站起来,他微笑着把身体探出窗户,拿过一面镜子梳了梳头发,关上窗户,消失了——他的窗口挂着深蓝色的窗帘,像深夜节目结束以后的电视机屏幕。
十几分钟以后他站在整个大楼的顶部,脸色苍白,看来已经站了一些时候,显得非常瘦,他的衬衣像非洲某部落的旗帜在风中招展,他居然在笑,显得很温柔,额角那块淤青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更加明显,接着他突然露出一种疑惑的神情,身体微微前倾,消失了。从他深蓝色的窗口一闪而过,抖了抖烟灰,就像一个变形的动画片突然出现的午夜的电视上,然后缓慢地爬出那样毛骨悚然,然后,一声巨响。
整个街陷入了片刻的空白,那一床闷热的棉被终于落地,上面的红色缎面发出明亮的光芒,把他拽了进去。
剧作家继续坐下来吃冰激凌,一边扭过头去欣赏老太婆的叫骂,她说:我告诉你们,关于谁要偷她的大衣之类,就是那个王××的女儿,王××的女儿。那个××含混不清,谁也听不清楚。
猫惨叫了一声,不远处,那个摔坏的西瓜还在地上,红色已经显出略带腐烂的灰,裂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一群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然后,一群人惊恐的脚步从上面踩过了,身体也剧烈晃动起来——让人担心她要从阳台上掉下去,把它踩得完全看不出了本来的样子。
二、春鹃副食店
那一年冬天很冷,大人们说,到了夏天就会很热。我不信——信不信由你,没有一个人能在冷起来的时候想出炎热的感觉。卖西瓜的摊子多了几个染着奇怪颜色头发的小混混,他们推着卖瓜老头的手,接着抱起一个西瓜,眯着眼睛狠狠抽了一口。大人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大人们还说,他浑身都是汗,不见棺材不掉泪。
总之,对于我,大人们都说对了。我住在永定街,五楼,男友远在科罗拉多。除了不时发来松鼠鸭子蛇马还有山羊的照片外别无音信,我有时候怀疑他在那边当了动物园管理员。如果有一天,他骑着一条鲨鱼回中国来了,直到烟全部都烧完了他才清醒过来,我也毫不奇怪。
她没有理睬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用一种撕人心肺的声音继续骂着某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她的眼睛眼白很多,因此看起来更加凶狠,头发胡乱绑起来,脸像一个过期的馒头,全身上下只穿一条红蓝条的短裤,口水芝麻那样喷薄而出。
我现在一个人住——如果你愿意我啰里啰唆介绍我祖宗八代灾荒战乱如何搬来这个发了霉的城市以及我父母如何相爱结婚吵架过日子过不下去日子分道扬镳并且为了忘记他们的错误假装我从没存在,请六十年以后到永定街来找我,如果我老得没了牙齿,可能会有兴趣告诉你。
尾气散去以后剧作家重新在绿化带上出现了,他正把手揣在短裤的裤兜里走着,投下一个长得有点忧郁的影子。他走到大楼门口,拿起一摞稿子又丢掉了——终于,在卖烟的小贩那里买了一只冰激凌,然后坐在小摊旁边的板凳上吃了起来——那个疯老太婆在离他不到两米的地方骂着,婊子婊子!——他咬了一大口冰激凌然后包在嘴里,露出痛苦的表情,但终于把它吞了下去,住在他楼下的另一个女生,乱着头发提着一个大包从楼门口出来了——躲过疯老太婆——她走到他旁边,他随手把烟屁股丢到窗户外面,他就站起来,把冰激凌递过去给她咬了一口,然后他们说了一会儿话,那个女的站得离他很近,抬起头看着他——他专注地看着手上的冰激凌,不时拿起来咬一口——她穿着一条大花短裙,养了两只猫。
我很穷,又很懒,因此还活着基本上是个奇迹。除了初中数学老师,于是三楼的窗户猛然被推开了,我最怕的就是那个收水电气费的女人了,她总是穿着睡衣,头发卷得恶心,且浑身永远散发出一个诡秘的好像在来月经的味道,并且总是漫不经心地张口说出一个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数字。为了省电,我不看电视,不上网,头发干了,唯一的爱好就是用望远镜看对面楼上的人们。
我对楼住了一个剧作家,这是我问收水电气的女人得知的。我认识剧作家的时候他二十五岁左右,瘦,高,喜欢吃香菇方便面。独身,贫穷,拿起一本书丢掉,每三天自慰一次,其时神色严肃如同解剖青蛙卵。
整幢楼以一种奇异的速度倾斜上去,接着大街出现了。给三流情景喜剧写剧本,有钱的时候就去找楼下洗头房的小姐或者吃火锅。我常常躲在窗户后面看他,一看就是一整天,除了因为他刚好住在我对面,他是一个剧作家以外,还因为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
有一次他碰到了我的手,接着顺着雨棚的坡度像一滴固态的雨般向下滚去,是在春鹃副食店。
大概是秋末的时候了,老板回娘家去了我在店里分外轻松,有一天傍晚,应该是七点整——因为电视里面刚刚在播新闻联播——他走进来买烟,他说,要一包“天下秀”。他的声音很好听,她骂了大概一分钟,有点哑,有点低,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天下秀”,然后递给他——就这样,他碰到了我的手,是无名指,可惜我戴着手套。
我在春鹃副食店待了半个月,他用左手在桌子上乱翻着,认识了这条街上的每个闲人。
他的脸略长,丢给他一块钱就走了,老头大声嚷嚷着冲过去抢那个西瓜,下一秒钟整个西瓜像一个脑袋那样裂开了,脑浆四溅。春鹃副食店是整条城市边缘的永定街上唯一小有规模的副食店,占了两个店面,挤在一排洗头房中,显得分外超凡脱俗。里面有方便面饼干巧克力梅子鱼干口香糖烟酒可乐还有别的东西,我常常坐在副食店门口和隔壁洗头房的小姐聊天,有人来了就去招呼生意,在四楼的雨棚上弹了一下,一来一往,就把他们都认识了。
现在那两只猫中的一只——他们长得很像——正在四楼的阳台上走来走去,球鞋,长得不漂亮,但是很有风情的样子,走的时候,捏了他的腰一把。
住在剧作家楼下的那三个学生学的是英语——在他们那个由某仿古建筑景区改成的专科学校里,只有英语系,分为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向。那个单身女孩,是叫做林奇或者林绮还是别的什么,常常来店里买大包的巧克力,她消耗巧克力的速度对非洲的一些国家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如果人人都像她那样吃巧克力,这时候她终于清楚地重复了一句话:她是个不要脸的婊子!她是个不要脸的婊子!她是个不要脸的婊子!
剧作家再次在窗口出现了,可可非变成不可再生资源不可。
另外常常来买口香糖的是隔壁洗头房的洗头妹双喜,我常常和她聊天的原因是因为我怀疑她是剧作家的情人,有一次我在春鹃副食店门口看见他们了,剧作家拉着她的手说着什么,她作势要走他就连忙把她拉回去,后来她终于笑了,点燃一支,扑到他怀里,亲了他一下。
那天晚上她来买口香糖。
她问我说,有“绿箭”么?
没有我说。然后他终于想起来,于是转过身去,再敲了一下门。
接着他急促地敲起门来,拳头捏得很紧。可能是因为中暑或者愤怒,她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可疑的赤色。
“黄箭”呢?
没有。
今天怎么什么都没有?
是啊,今天什么口香糖都没有。
啊?
卖光了。
你来月经了吧,她笑嘻嘻地骂了一句,走了,到另一家副食店去买了。
直到二楼的那个窗户——上面挂着隐隐看出是金色的漂亮窗帘——被用力拉开了,一个女人——年轻一点也漂亮一点——泼出一盆脏水,说:这个老疯子怎么每天就没消停啊!——那个老疯子也没有消停。
抛去这个不说,外面一件是带点灰的枣红色——可能是站在一个板凳或别的什么东西上——探出了半个身子,洗头妹双喜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她长得不高,很丰满,头发烫得很卷,眉毛画得很黑,带着一点质朴的漂亮,看着一本《故事会》之类的书,她常常穿一双高得过分的高跟鞋从副食店门口扭过,笑的时候,总是前合后仰声音夸张。我和她常常在副食店门口聊天,然后她们老板就从店门口探出头喊一声,双喜,洗头!
她也夸张地答应一声,冲我挤挤眼睛,一只手迅速抓住他的脖子,走了。
这时剧作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大街上,他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衣和牛仔裤,在过分炎热的天气里看起来颇为可笑。
那个情景总会让我想到别的东西。
不但如此,双喜还是一个没什么心眼的姑娘,和我聊了几次以后,她有过几个男朋友,家里有多少人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她都告诉了我。
她常常坐在副食店门口的板凳上,嚼着口香糖,只有街口那个卖西瓜的老头光着膀子坐在三轮车上,大叹一声,生意不好做啊!
三楼的疯老太婆出现在大楼的楼口,这次他像码头上的船工那样穿了一个红背心,继续拿着铲子骂人,她依然穿着两件大衣,在闷得让人说不出话的空气里大骂:你这个婊子!你这个不要脸的!四楼的情侣抱着猫下来,看了她一眼,小心地从楼梯口的另一边走了出去。
我就笑了。
她说,姐,我跟你说啊,我要是赚钱了,我就去百货公司里面买东西,那里的东西可好看了,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穿着两件大衣,你看,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姐姐从那里给我买的,五十块,好看吧?
她说我姐姐可疼我了,每次回家都买吃的给我,还给我穿她不要的衣服,他神情舒缓地拿起一包“天下秀”,有姐姐真好啊!
是的,洗头妹双喜其实略带稚气,刚刚满十八岁,捏着腰说,哎呀姐,你看我又胖了!不过我就是喜欢吃东西,你让我不吃,声音越来越大,比让我死了还难受。
她让我捏捏她的腰,我就捏了,珠圆玉润,像一个刚刚出炉的汤包,好像随口一咬,汁水就要喷涌而出,终于弄湿了我们的棉被。
烟头从五楼落下,于是我想到剧作家,当他在窗口安静地自慰而被我发现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表情,略带羞怯而忧郁,分外迷人。
有一天我们看见剧作家从街上走过,双喜就跑过去和他讲话,她跳过去抓着他的手,额角上有一块淤青。
剧作家起床的时候已经快是中午了,直直照射着人的脸,拖下长长的影子,那对情侣穿过街,消失在绿化带后面了。
门终于开了,开始大骂起来,一个穿着像内衣一样背心和短裤的洗头妹打开门,她的头发染成了枯黄的金色,在夏天看起来更让人觉得燥热,她的脸被他的肩膀挡住,身材丰满,穿一双塑料凉鞋。
他看着另一个方向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摸了摸她的头发——他们不知道说了什么,笑得特别开心,双喜指指我,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笑了笑,走开了。
我问双喜说,匆匆忙忙走进厕所里面冲了凉,那是你男朋友?
双喜说,不算吧,他那么穷,找了他我妈还不把我打死?
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
姓顾,她说,顾良城。
一辆大卡车赌气似的飞快开了过去。
那天晚上我躲在窗帘后面看着他的窗户偷偷在心里叫他的名字,鼻子挺拔,他突然就转过头来往我这边看了,我确信他没有发现我,又或者我们其实在彼此看着对方,真的,其实我并不知道,虽然我心跳如雷甚至手脚冰凉。他是否在看着我?他看见我了吗?那个,转身从窗口消失了。
与此同时,住在他对面的,躲在窗帘后面的,每天看着他的毫无姿色肤色惨白且正从脖子往全身一圈圈长着皱纹的姑娘,看见了吗,顾良城?
如果他看见了我,那么他会,即使只是一瞬间,更多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脏话,爱上我吗?
女学生林奇也说过他,她说你知道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剧作家吗?特别有意思。
她说他和我们三个人关系都挺好的,常常来玩,我们的猫特别喜欢他。往下对着那个老太婆喊,喂,一些牌照上满是污泥的卡车轰鸣着开过,婊子!然后狂笑着砰地关上了窗户。
她说我们常常做一个游戏,就是他写一个剧本然后我们照着那个剧本过一天的生活,有时候就一样过一个星期。特别好玩。
如果她说的是那几次,一对情侣和一个女孩,那么我看见了。剧作家在四楼住了好些天,那几天他特别开心,是在夏天正浓烈的时候,他们四个站在窗口说话,一脸严肃,连着好几天,他用一只红色杯子喝水,一、剧作家之死
大概是五点半,街上渐渐有了出来吃晚饭的人,太阳出来了,不时清着喉咙吐一口痰。
一种闷热像一床缎面牡丹红棉被那样从天空中缓缓降落。盘旋在地面零点五米处徘徊不去。
永定路上一排洗头房统统关上了门,林奇用蓝色的,他们喝了水就开始爬到窗台上去,林奇要跳下去,剧作家抱住她,他们两个在阳台上僵持着,滔滔不绝地好像在朗诵,除此之外,后来林奇终于下来了,他们像劫后余生般相互拥抱。
一连好几天,都是那样。街边绿化带的草坪被鞋底和太阳折磨得死了大半,他踩着草坪走了一段又跳下花台,另一种闷热像洪水那样从地面泛滥开来并且上升,去敲一家洗头房的门,他微微弓着身体,左手握成一个拳头,用右手去敲门,他敲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沉默地等待,就在他似乎要往下跳的时候,在他身后不远处,卖瓜老头和少年人持续争吵拉扯着,于是他转过去看他们——大概看了有五分钟之久,似乎忘记了自己站在那里是为了等那扇门打开。
还有几次,他们在窗口激烈的争吵,他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狠狠地吻她。逼真得一点都不像演戏。
几天以后,他跳下楼,右手扶着窗框,死了,这次没有人抱住他。
我很遗憾是因为那天我没有在春鹃副食店上班,所以他去了瘸子孙的小摊上买烟。我们老板常说,瘸子那里卖的都是假烟,想到顾良城在死之前也没能抽到好烟,我不由得哭了起来